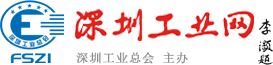首頁 > 品牌建設(shè) > 品牌觀點(diǎn)
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作為中國優(yōu)秀企業(yè)的代表,其一舉一動(dòng)都備受外界關(guān)注,特別是在企業(yè)戰(zhàn)略決策和經(jīng)營管理等方面的理念與模式都成為眾多渴望成長企業(yè)效仿的楷模,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的創(chuàng)始人一度為媒體稱為中國企業(yè)的管理“教父”。所以研究中國企業(yè)在管理方面的進(jìn)步,就不得不關(guān)注聯(lián)想的變革。
如果將聯(lián)想視為中國企業(yè)管理水平的標(biāo)竿,肯定有不少的非議。但是僅就企業(yè)的戰(zhàn)略管理方面而言,聯(lián)想無疑都走到了大多數(shù)企業(yè)的前面。從廣為傳播的聯(lián)想管理三要素“建班子、定戰(zhàn)略、帶隊(duì)伍”,到聯(lián)想數(shù)度斥資聘請國際一流的管理咨詢公司制定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,再到每年一度的上上下下齊動(dòng)員的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制定,以及以柳傳志為代表的聯(lián)想高層在不同場合對于戰(zhàn)略的詮釋等,都表明無論是對于戰(zhàn)略的重視程度,還是對于戰(zhàn)略執(zhí)行的強(qiáng)調(diào),聯(lián)想都無愧于是中國企業(yè)的佼佼者。
但是,我們不能苛刻的要求聯(lián)想不能一點(diǎn)錯(cuò)誤都不犯,更不能神話聯(lián)想一點(diǎn)錯(cuò)誤都不會(huì)犯。聯(lián)想在戰(zhàn)略管理方面也還是有值得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(yàn)的地方,同樣也需要更多的中國們認(rèn)識(shí)到作為一個(gè)優(yōu)秀企業(yè)必須要在戰(zhàn)略上盡可能的減少失誤。
聯(lián)想的最近一次的整體變革以“業(yè)務(wù)更加專注”、“更加客戶導(dǎo)向”及“提升運(yùn)作效率”為三大目標(biāo),最為重要的內(nèi)容是關(guān)于現(xiàn)有業(yè)務(wù)的重新劃分和界定,即分為核心業(yè)務(wù)、重點(diǎn)業(yè)務(wù)和其他業(yè)務(wù)。其中核心業(yè)務(wù)為PC及相關(guān)產(chǎn)品,重點(diǎn)發(fā)展業(yè)務(wù)為移動(dòng)通訊產(chǎn)品,IT服務(wù)和網(wǎng)絡(luò)產(chǎn)品都?xì)w于其他業(yè)務(wù)。
對于業(yè)務(wù)的選擇屬于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的核心內(nèi)容,戰(zhàn)略就是要在“做什么”和“不做什么”之間作出選擇。回想2001年4月聯(lián)想“新政”時(shí)期發(fā)布新戰(zhàn)略的時(shí)候,我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聯(lián)想要積極的“做什么”,確定了企業(yè)IT、消費(fèi)IT、手持設(shè)備、IT服務(wù)、合同制造、信息運(yùn)營6大業(yè)務(wù)群組。而這一次卻是謹(jǐn)慎的選擇“不做什么”,回歸到以PC與移動(dòng)通訊產(chǎn)品兩大業(yè)務(wù)為主的“二元化”道路。
從“多元化”到“二元化”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著是對2001年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的自我否定,也可以認(rèn)為是企業(yè)決策者在戰(zhàn)略選擇上逐漸成熟的體現(xiàn)。姑且不論聯(lián)想的這次變革是否從根本上解決了聯(lián)想未來5年甚至更長時(shí)間的戰(zhàn)略問題,僅就敢于自我否定這一點(diǎn)來看,也充分體現(xiàn)了聯(lián)想決策管理層的自信和勇氣。
盡管聯(lián)想在變革的時(shí)候采取了非常堅(jiān)決的手段,也使得變革過程中的風(fēng)險(xiǎn)降低到最小。但是,回顧2001年以來聯(lián)想如此巨大的戰(zhàn)略調(diào)整,無論是資源的有效利用,還是機(jī)會(huì)的把握,甚至是對的提升都會(huì)帶來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。聯(lián)想的變革可以說是主動(dòng)的,也可以說是被迫的。無論怎樣,都反映出以聯(lián)想為代表的中國企業(yè)在戰(zhàn)略制定和戰(zhàn)略執(zhí)行方面的不足。
如果說聯(lián)想在戰(zhàn)略制定上存在不足的話,可以明確的體現(xiàn)在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的制定上。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的制定是要結(jié)合企業(yè)領(lǐng)導(dǎo)人的發(fā)展愿望,但是更多的還是要考慮到市場需求的變化和自身能力及資源的匹配。當(dāng)時(shí)的聯(lián)想正是新老交替的關(guān)節(jié)點(diǎn),無論是老一代的企業(yè)家,還是接班的新一代企業(yè)家都對于聯(lián)想的未來給予了更高的期望,投資人也希望有更理想的回報(bào)。另外在2000年對于聯(lián)想而言,業(yè)績驕人,年中上調(diào)指標(biāo)的局面也意外出現(xiàn)。這些因素在新一代接班人強(qiáng)烈的成長愿望面前都被不恰當(dāng)?shù)姆糯螅瑢?dǎo)致在第一次主導(dǎo)制定三年戰(zhàn)略目標(biāo)時(shí),對于即將出現(xiàn)的IT行業(yè)變化估計(jì)不足,同時(shí)在鮮花和掌聲中過高的估計(jì)了自身的資源和能力。
“在2001財(cái)年,我們將實(shí)現(xiàn)超過260億元人民幣的營業(yè)額,2003年達(dá)到600億元人民幣的營業(yè)規(guī)模,力爭進(jìn)入所參與領(lǐng)域的市場前三名。”這樣的目標(biāo)在當(dāng)時(shí)也更多的是激情的產(chǎn)物而非理性的選擇。
在這樣的目標(biāo)指引下,面對PC日益透明的環(huán)境,尋找在相關(guān)行業(yè)的突破變成了聯(lián)想當(dāng)時(shí)多元化戰(zhàn)略選擇的必然。作為聯(lián)想這樣的企業(yè),局限于PC產(chǎn)業(yè)明顯不是最優(yōu)的選擇,而聯(lián)想當(dāng)時(shí)所選擇的六大產(chǎn)業(yè)群組也是在對美國市場充分調(diào)研的基礎(chǔ)上,結(jié)合國際咨詢公司的指導(dǎo),從幾十個(gè)信息相關(guān)行業(yè)中按照嚴(yán)格的標(biāo)準(zhǔn)挑選出來,也確實(shí)考慮到不同產(chǎn)業(yè)之間的接替,不能說不慎重。事實(shí)上,在聯(lián)想原來選定的六大行業(yè)中,都不乏成功的案例,比如門戶網(wǎng)站、比如消費(fèi)IT、IT服務(wù)等等。這樣,一方面作為聯(lián)想這樣的企業(yè)需要有足夠的市場空間,必然會(huì)在相關(guān)的行業(yè)積極尋求拓展,另外一方面當(dāng)時(shí)所作出的篩選也是非常慎重的,以聯(lián)想的作風(fēng)相信不是盲目的拍腦袋決策。
所以,從這個(gè)角度來看,聯(lián)想的戰(zhàn)略問題不在于業(yè)務(wù)選擇多寡問題,而是總體指標(biāo)訂得太高,造成所有業(yè)務(wù)都開始大躍進(jìn)式的發(fā)展而忽視了不同業(yè)務(wù)之間在客戶需求、消費(fèi)特點(diǎn)、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差異性。這一次的大規(guī)模的收縮也許又走向了另外一個(gè)極端,或許并沒有解決聯(lián)想未來的長遠(yuǎn)發(fā)展問題。因?yàn)閮H僅是PC和手機(jī)仍然滿足不了聯(lián)想的成長要求,況且這些領(lǐng)域的增長和利潤空間已經(jīng)非常有限,即使聯(lián)想成為每一個(gè)領(lǐng)域的老大,市場份額的增長也是有限的。
聯(lián)想在戰(zhàn)略管理方面的另外一個(gè)值得更多企業(yè)吸取教訓(xùn)的是仍然在戰(zhàn)略執(zhí)行方面存在的問題。對于戰(zhàn)略執(zhí)行的理解,如果僅僅局限于對一個(gè)制度的貫徹是否迅速徹底,不免有些膚淺。對于聯(lián)想也是這樣,如果從聯(lián)想的員工素質(zhì)、執(zhí)行政策的力度等方面來看,聯(lián)想的執(zhí)行力可謂是出類拔萃,但這并不是戰(zhàn)略執(zhí)行的全部。比如管理模式問題,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和聯(lián)想控股都有投資的功能,但是二者的區(qū)別在于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更多的是在從事產(chǎn)業(yè)投資而非風(fēng)險(xiǎn)投資。那么作為產(chǎn)業(yè)投資主體的聯(lián)想集團(tuán)總部應(yīng)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?是直接的經(jīng)營者還是戰(zhàn)略的制定者,還是二者兼?zhèn)?作為承擔(dān)主體的各個(gè)業(yè)務(wù)群組,必要的經(jīng)營管理職能是否具備?集團(tuán)對于不同的業(yè)務(wù)管理是考慮到了不同的管理深度?再比如團(tuán)隊(duì)問題,不同的業(yè)務(wù)群組需要不同類型的管理團(tuán)隊(duì),特別是新的業(yè)務(wù)需要?jiǎng)?chuàng)造性和偏執(zhí)狂的精神,就像TCL當(dāng)年的萬明堅(jiān)一樣。但是聯(lián)想的團(tuán)隊(duì),無論是哪一個(gè)業(yè)務(wù)群組,都是聯(lián)想管理三要素的堅(jiān)定執(zhí)行者。回想當(dāng)年參加IT1FOR1的戰(zhàn)略發(fā)布會(huì),聽到更多的還是三要素,而不是更多的如何在市場上獲得勝利的謀略。聯(lián)想的斯巴達(dá)克方陣確實(shí)有可以圈點(diǎn)的地方,但是如果所有的業(yè)務(wù)單元的經(jīng)營管理層都是一樣的思維模式,在終端上還是會(huì)體現(xiàn)厚重的PC色彩。也就是說,聯(lián)想也許是在按照經(jīng)營PC的套路在與不同的對手展開競爭。
聯(lián)想新一輪的變革必然會(huì)在短期內(nèi)提升PC的銷量,也會(huì)使得下一季度的財(cái)務(wù)報(bào)表得到投資人更多的贊許,但是這一次的聯(lián)想變革更多的還是在銷售管理上的變革和深化,這種“劃小區(qū)域,深耕細(xì)作”方式在彩電業(yè)也早已有之,并不新鮮,也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未來更長時(shí)期的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問題。
中國要產(chǎn)生偉大的企業(yè),必須要在對待戰(zhàn)略的態(tài)度上更加成熟和理性。聯(lián)想尚且如此,不得不讓人為其他更多妄稱“優(yōu)秀”的企業(yè)家感到擔(dān)心。
對于聯(lián)想,我們依然有更多的愿望和期待。